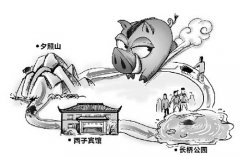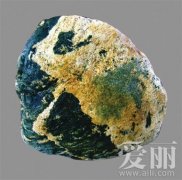故宫国宝迁徙中的护宝人:典守故宫国宝70年(3)
清华学堂的学生刚报到时,有人看到一位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神情有些萎顿的老人,便悄悄打听:“这大概就是李济先生吧?”其实那位老先生是王国维,在青年学生心目中,研究考古的必是位老先生,而李济那一年才29岁。
1926年10月,李济率队来到山西夏县西阴村做田野考古工作,这次发掘收获非常大,采集到了60多箱出土文物,大部分是陶片。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的挖掘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发掘中最有趣的发现是半个蚕茧壳,壳上有平整的人工切割的痕迹。经专家鉴定,那半个蚕茧壳确实是一种家蚕的茧,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这次发掘之后,李济撰着了《西阴村史前遗存》,这一着作奠定了李济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地位。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当时的所长傅斯年一开始就定下了两件事:一、成立一个组,以考古学家作为研究中国史的新工具;二、以发掘殷墟作为考古组的第一个田野工作项目。他需要一个合适的学者来领导考古组。最后傅斯年选择了李济,从那时开始,李济的一生和安阳的殷墟发掘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发掘之初,李济跟所内同仁约定:一切出土物全部属于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仁自己绝不收藏古物。
殷墟的发掘工作一直持续了15个工作季,直到1937年中结束。在第三次挖掘时,发现了着名的“大龟四版”,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占卜文字。1935年,殷墟第11次发掘为期95天,所获极多,出土了牛鼎、鹿鼎、石磐、玉器、石器等多件文物。殷墟大发现震惊了世界,也是李济一生事业的黄金年代。
殷墟发掘印证了商朝的存在,并由此把中国的历史向前推了几百年。李济的学生张光直曾说:“直到今天,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仍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
1937年,在殷墟第15次发掘收工后仅18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已经接替傅斯年担任中央博物院(中博)筹备处主任的李济,负责“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博”向西南搬迁之事。
“史语所”在昆明安顿了两年后,因滇越线战事吃紧,又从昆明迁往四川李庄。李庄6年,生活虽然困难,但李济带领着考古组依然坚持考古工作,曾在四川彭山崖墓发掘出一些重要石刻和特殊雕刻,还和四川省博物馆合作,在成都琴台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
战乱期间,李济的两个女儿均因医疗条件太差患病去世,只剩下一个儿子李光谟。之后李济夫妇过继了一个亲戚的男孩,取名“光周”,后来也成为一名考古学家。
1948年内战爆发,许多文物刚从大后方运回南京,还来不及开箱,又要搬到台湾。安阳殷墟文物也在转移之列,李济是这次迁徙的押运人。
当时很多人反对文物搬迁,李济心里也很矛盾,但他第一考虑的是保护文物,他说:“只要文物是安全的,无所谓去哪个地方。”为了文物,李济决定携妻儿迁居台湾,但他的儿子李光谟不愿意,他决定回上海。李光谟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次分离就是永别。
李济到台湾后,很快筹备成立了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培养了不少优秀的考古及人类学人才,其中最突出的是张光直。张光直出国留学,成就非凡,38岁升任耶鲁大学教授,48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后来又在65岁时获美国亚洲学会终身杰出成就奖,这是中国考古学者获得的最高国际荣誉。
到台湾后的李济多少有些落寞,因为台湾无多少古可考。在晚年行动不便时,他仍然坚持每周拄着拐去看台北故宫里的文物。台湾青铜专家陈芳妹回忆:“在青铜器前,他仔细端详,神情专注,不厌其烦,犹如古生物学家对化石的深入细微。”
1977年,81岁高龄的李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综合性学术着作《安阳》,为一生的学术研究划上了句号。两年后,李济心脏病发,在台北逝世。
1995年,李光谟赴台湾把父亲的手稿、信件和资料运回了北京。2006年,李光谟花了8年时间编纂整理的五卷本《李济文集》出版。在对李济资料的整理中,李光谟逐渐理解了父亲对考古的感情,感受到了父亲作为一名考古学家的生命能量。

庄严——一位“老宫人”的两件憾事
“宣统出宫,我便入宫,当的不是皇帝,而是一个维护民族文物国家重器的老宫人……”这是庄严于1969年8月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上退休时说的一句话。这位“老宫人”1920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经北大教授沈兼士推荐,担任“清室善后委员会”事务员,之后在战乱时期一路护送文物,历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安顺办事处主任、巴县办事处主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及副院长等职,为故宫博物院整整服务了45个年头。为此,他曾自豪地宣称“从一而终,亦不过甚”。
庄严的一生是随着故宫文物的颠沛流离过来的,故宫文物走到哪里,他便跟到哪里。自入故宫之日起,庄严先生便秉持着文物乃“学术公器”的理念,并将之贯彻一生。1926年春,28岁的庄严与同事合作,用故宫特制的纸张与印泥,将宫中所藏古代铜印1295方全部手钤,汇编26部,定名《金薤留珍》。这本印谱售价高达银洋100元,却深受欢迎,后来还一版再版,足见其意义。
“九一八”后,故宫文物南迁,庄严参加了各种不同文物的装箱和迁运工作。从2月到5月,文物前后共分5批从北平运出,辗转到上海,分别存放在法国和英国租界。1936年,南京朝天宫旁的永久保存库修建完工,于是原存上海的四单位文物,便在当年底,全部用火车运到南京新库存放。
“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文物分三路西迁大后方。庄严押运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的80箱精品,先是借湖南大学图书馆暂存,再从长沙经广西桂林到贵州。他的妻子及3个未成年的儿子跟着他辗转奔波,他的第四个儿子庄灵出生在贵阳。最后,文物运到黔西安顺县城外的华严洞内存放。庄严全家在安顺县城内东门坡一幢木造民宅中寄居了将近5年。
当时贵州贫困,战时物资缺乏,生活更是艰苦。庄严和同事的薪水常常无法按时汇到,为此妻子还得每天走好几里路到城外黔江中学去教国文以贴补家计。庄严的儿子庄灵回忆:“当时吃的都是夹杂着谷壳稗子和石粒的‘八宝饭’,下饭的菜主要靠辣椒粉和酱油;穿的衣服全有补丁;书籍都是用发黄的‘毛边纸’印的;晚上全家人看书和做功课,桌上只有一盏燃烧菜油和灯芯草的‘灯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