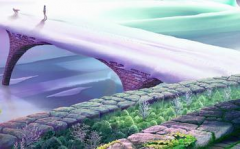情深言淡汪曾祺|逝世20周年

汪曾祺 图/陆中秋
“ 有人让他用一句话概括他自己,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汪曾祺的长子汪朗在这个母亲节回忆起自己的父亲,他常常直呼之为“老头儿”:老头儿在家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平等,每天为家人买菜做饭,从不把工作中的情绪带回家里,早上起来,给自己做一碗改良版的高邮阳春面,喝一杯茶便开始写作。“虽然今天是母亲节,但我在这里谈起父亲也是满满的爱。”母亲节后再过两天,就是汪老辞世20周年的日子了。
高邮
这种平等,沿袭自汪曾祺的父亲。汪曾祺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往往给汪曾祺也倒上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儿子一根老子一根,老子还给儿子先点上火。汪曾祺17岁初恋,在家里写情书,父亲在旁边跟着瞎出主意。“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家其实规矩很大,汪曾祺66岁那年回乡,第一件事就是回家拜望继母(任氏娘),还没进家门,老头儿在门外的水泥台阶就跪下了,要给任氏娘行跪拜礼。继母一把挽住他说,“曾祺,不可,你也是见孙子的人了。”汪曾祺却很坚持:“那不行,这是汪家的规矩。”
汪曾祺祖籍安徽,出生在高邮,汪家大院在高邮很有名气,祖父汪嘉铭在当地做药材生意,“万全堂”和“保全堂”口碑都很好,汪曾祺小时候几乎天天都要去祖父的药铺玩耍,他的小说《异秉》,写的就是保全堂。
汪曾祺的祖父在清代末次科举里中了“拔贡”,废除科举后,功名道断。汪曾祺的父亲则在南京上过十年一贯制的旧制中学,“旧制中学生”也算功名,用泥金扁宋字写在汪曾祺亡母出殡的铭旌之上。汪曾祺幼从家学,练字的《圭峰碑》《闲邪公家传》等,都是初拓的珍本,来自祖父的收藏。晚年汪曾祺鼓励后辈学作近体诗,还常用当年老太爷的原话,“文从胡画起,诗从放屁来。一开始总写得不成样子,写写就好了。”
1948年冬,汪曾祺与夫人施松卿
汪曾祺上的是新式小学堂,但从小耳濡目染,也学习古典诗文,能诗能画,兼谙乐器戏剧,这些广泛的兴趣爱好,都来自他的父亲。李渔说,“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如果此说成立,那汪曾祺和他的父亲,都是一身癖好、用情极深之人。父亲是眼科医生,年轻时是运动员,田径好手,同时习武、骑马,水性好,笙箫管笛、琵琶、月琴、胡琴、扬琴,无一不会,同时画画、刻章,一双巧手,还会给孩子做灯笼和扎风筝。汪曾祺的生母过世,他亲手为她糊了一箱子纸衣服,单夹皮棉,甚至糊了几可乱真的皮衣,分得清滩羊、灰鼠,好让自己的太太在九泉之下四时不缺时髦又暖和的衣衫。妻子死得早,他因此格外疼爱她留下的这个孩子,汪曾祺小时候,是个惯宝宝。少年时外出考学,父亲送他去,旅馆床铺有跳蚤,父亲一宿没睡,拿着蜡烛在旁边守着他,发现一只跳蚤,就用蜡油滴死一只。汪曾祺醒来一看,席子上满满全是蜡油点子,自己却美美地睡了一整夜。
在父亲的影响下,汪曾祺金石篆刻、曲艺乐器,样样精通,对他来说,这都是玩儿,“生活,是很好玩儿的。”晚年自娱是做菜,也爱写吃食。当时北京城中文化人物宴聚,王世襄的焖葱固然让人眼前一亮,汪曾祺的干贝吊小萝卜,也让远道而来的聂华苓连汤底都喝了个干净。
联大
如果给汪曾祺的写作设几个关键词的话:高邮、西南联大、张家口、北京是四个绕不过去的坐标。此人念旧,而且长情。写来写去,皆是故乡、故人。
战时的西南联大,云集了中国最一流的大脑,西南联大的大学生活,对汪曾祺来说刻骨铭心,他称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为“第二故乡”。沈从文、闻一多和杨振声都很器重他,尤其是沈从文,视他为得意门生。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左起:李荣、汪曾祺、朱德熙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就读于中文系,在校时他并不用功,自由散漫,常常逃课去逛翠湖,但是阅读极广,颇富文名。他与穆旦、鹿桥被认为是西南联大培养的最有才华的作家。
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汪曾祺文风受沈先生影响极大。青年时期,汪也很喜欢抖机灵的写作方式。某次写了篇小说,主人公的对话十分精彩,格外精心设计过,但是沈从文却批评他:“你这不是人在讲话,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
汪曾经写过不少怀念沈先生的文章,尤其记到一个细节,他常常从沈先生那里借书看,有一次,在书的某页,看到沈先生题了一笔:某月某日,见一个大胖女人过桥,心里很难过。这条笔记让汪曾祺揣摩良久:这是个什么大胖女人,为什么沈先生看见了大胖女人会很难过呢?这一师一徒徒劳心事,均折射出某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

1961年,汪曾祺与沈从文在北京中山公园
晚年汪曾祺写出他的代表作《受戒》后承认,在他写小英子这个人物的时候,他脑子常常想的是沈从文笔下的那些农村女性:三三、翠翠、夭夭。
西南联大时期正值战时,物力艰难,最初,汪曾祺还有带去的一点钱,可以吃馆子、骑马,过浪漫主义的生活,后来就穷得叮当响。为生活计,汪曾祺曾在昆明北郊的中国建设中学教了几年书。他专门写过这段囚首垢面、食不果腹的贫穷时光,他没有说出来的是,也正是在这几年中,他结识了同在建设中学教书,也同为西南联大校友的施松卿,两人此后相伴一生。施是外文系的毕业生,父亲是马来亚的侨领。跟汪家相仿,施松卿的父亲也做药房生意。汪曾祺的子女曾经打趣母亲:你不是说当时中文系的学生都土得很吗?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施松卿说:“有才,一眼就看得出来。”
比同时代的很多文人幸运,汪曾祺的家庭和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风雨飘摇中,家庭成员之间也并未隔阂反目。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很长时间不能见到孩子,回家后,子女跟他依然很亲。母亲有时出于爱护子女前途,策略性地让孩子跟爸爸“划清界限”,孩子就反过来揭穿妈妈:“那你怎么还给爸爸打酒喝?”
右派
汪曾祺曾在随笔中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1958年,因为系统内“右派”指标不够,汪曾祺“补课”成为右派,斗争来势汹汹,大字报贴满了单位过道,批判会一开再开。“我规规矩矩地听着,记录下这些发言,这些发言我已经完全都忘了,便是当时也没有记住,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的、虚空的对象。”
他曾经发表过一组短诗,里面有一首《早春》,描摹新绿朦胧,有“远处绿色的呼吸”这样的词句。不讴歌红而讴歌绿,这也成了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