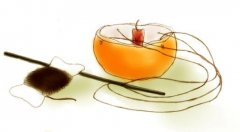《中国散文家》2016.6期“梦到了那个叫五里的地方”(2)
许多珍贵的照片,为我们定格了历史的真实。照片里,那些有着50岁面相的民工,其实只有30来岁的年纪,他们经历的是怎样的苦难劳作。照片里,分明看到人们的脸庞是浮肿的,当你还来不及感伤,你已经被他们灿烂的笑容深深地感染。
青年洞始终是红旗渠的一面红旗。1960年隆冬,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吃紧时期,全国多地,包括林县周边多地,出现了饿死人现象。中央指示实行“百日休整”,下令全国所有建设工程暂时下马,给人民一个休养生息机会。红旗渠也面临着下马。气可鼓不可泄,刚鼓起来的气一泄就不可收拾。县委决定留300名青年突击队员藏在山腹里开凿青年洞。杨贵的想法是,只要留下一个人在工地上,就把全县55万人的心留在了红旗渠上。洞中是青一色的火炼石,十几磅的大铁锤砸下去,石面只留了一个白点,一炮只炸个“鸡窝窝”,最初每天的掘进进度只有30厘米。“只要有一碗糊涂面条,浑身就都是劲”。智慧加毅力,热汗加热血,一年半的缠磨较劲,500个日夜的死嗑厮咬,616米长的青年洞终于打通了。
青年洞现在成为红旗渠景区的重要景点。最初来参观的外国人,实在是感到不可思议,有人以为这是个天然石洞,中国人只是修了个洞门。我乘快艇到洞中游览,满眼都是金属质感的石壁,始知外国人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如今,到过青年洞的有许多的外国元首和中国领导人,有更多的艺术家、科学家,有数不清的中外游人。全人类都在交口赞叹,红旗渠是“人工天河”,是“地球的蓝色飘带”,是民族精神的丰碑,是中华文化的鲜明符号……
青年洞口的崖壁上,镌刻着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题词:山碑。的确如此,只有巍峨的800里太行,才能足以担当红旗渠精神的丰碑。
梦到了那个叫五里的地方
◎ 周寿鸿
周寿鸿,江苏高邮人,扬州报业传媒集团编委、扬州时报副总编辑。作品散见于《雨花》《半月谈》《海外文摘·文学版》《杂文报》《杂文选刊》美国《侨报》等30多家报刊。曾获第三届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一等奖、第二届中华情全国诗歌散文联赛金奖。系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
不喜欢回首往事。往事就是一张网,满怀感情地撒下去,捞上来的却只是一汪水,很快便漏尽了。
昨天梦里,回到了那个叫五里的地方。许多年不做梦了,这个梦显得太清晰。梦里,我似乎想抓住什么,一伸手,梦便醒了。想抓住什么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个梦呢,我也不知道。
那个叫五里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是我最疼痛也是最美好的地方,是我今后终老和埋葬的土地。我在那里生长到15岁,从县城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回那里工作了6年多。后来,我坚决地不留丝毫挂念地离她而去,先上了县城,后又去了更大的城市。从离开的第一天起,我就把这段日子死死地锁起来,扔掉钥匙,生怕它再被打开。
记得刚上城的一年里,曾一次次梦见新单位解散了,我又被遣退回老家。一次次做同样的梦,一次次在梦里惊醒。那份对乡村生活的恐慌,像一只拳头,久久地攥着我的心。现在回想起来,心情已很淡远了。在城里安了家,接来了父母,很难得才回一趟老家。现在谈起老家,已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可是,我为什么还梦见那个叫五里的地方呢?
五里是一个小集镇,距县城80华里,距县里三大镇之一的临泽约8华里。父辈常说“十世修得城里人,三世修得镇上人”,临泽是我儿时最向往的地方。当时临泽只有一两条像样的街,古色古香:青古板路;仄逼的铺闼子,长长的进深,光线只能照进一个角落;卖香烛的,卖铁锅的,卖烧饼、桃酥和麻油馓子的……后来我写小说,这样的场景被用到了里面。现在,还能想见昔日的老街模样。
不过,常去的还是五里。集镇虽小,没有临泽的喧闹与繁华,却是最亲切的地方。家距五里只有不到3华里,父亲在镇里的农具厂上班,我有时放学后会过去玩,遇集镇放露天电影,也总是早早地赶去,垒上两块砖,圈定一方小小地盘。电影散场,急急往家里赶,弯弯小道被两边高高庄稼压得更小,到处是幢幢的影子。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走,终于看到村庄的灯光了,一颗心终于舒展开来。
五里虽小,但有一家新华书店,在集镇供销社隔壁。对于儿时的我,这是一个圣地。家里穷,除了缴学费,并不给我多余的钱,父亲偶尔出远门,我的要求不是带回一只烧饼或几块糖,而是一本小人书。到新华书店,并不是为买书,而是踮着脚,伸长小脑袋,隔着高高的柜台,看里面花花绿绿图书的封面。去得多了,又总不买,里面的店员,一位打扮得很洋气的女人有点嫌烦,我便有点怕她。有一次,很洋气的女店员到后面去有什么事,仿佛鬼使神差,我竟从书柜夹缝里抽出一本书——真不知道哪里来的胆量,那可是偷呢!得手后赶忙逃走,跑了老远,到了一个没人地方,把书打开,真是又惊又喜——这本《上下五千年》,当时还看不太懂,但打开了我童年的世界,所以至今难忘。
有好几个月,我都不敢去新华书店,后来憋不住了再去,那个店员并没有用特殊的眼神看我,一颗惴惴不安的心终于落了地。不过,不知道是心里有鬼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去五里书店的心情渐渐淡了,毕竟这里的书太少,而且不让翻,不像临泽的书店,书比较丰富,还可以去翻一翻。
对于五里的记忆,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工作后。我供职的小学校绿树成萌,我住在教办楼一楼最东面的一间,后面有一条河,旁边是空旷的操场。我让父亲打了一只书柜,放了满满几排书,将两张办公桌拼成一个大大的书桌。入夜,校园阒静无声,惟我独坐陋室,读书、备课、改作业、写文章,直至夜深。小学校前身是一个乱葬茔,有一段时间我喜读谈狐说鬼之书,屋外风高天黑,蓦然一抬头,恍忽窗户外面,一个俏丽女鬼正莞尔笑对,心里猛一激灵。哪里能有什么女鬼?只有呼呼的风声掠过树梢,投下摇曵的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