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期《散文选刊》抢先看(4)
不过,两兵相接的平常寒暄用语,内里可是大有文章的,一句“你今天从哪边卖过来啊?”就可从对方的口中知道哪些地方已经“沦陷”了,不需多跑一趟了,然后再看一看对方车上的货物,尚可评估他在那一带的顾客量如何。若在同一区错身,一句“生意怎样啊?”也可以暗自打量两人在同一村庄的客源如何。宣传车如同战车,但双方言语,才是主攻炮弹。
有时,顾客也会不自觉地加入战局,不小心进入了他军沦陷区,不但生意变少,还有顾客会拿着之前买的货物,抱怨我爸卖得比较贵,这时我爸可得动动脑筋,必须了解敌情,别人是如何削价竞争的。我爸笑着回应,与客人交换商品,用贵的换便宜的,任谁都不会有意见。带回家后,便会从商标数据探听,打电话询问,如果对方进货价格较低,二话不说,吸收进来,加入我方阵营。
我爸做生意,到访的都是偏远小村,村道上往往见不到几个人,两排是传统的土埆屋,稻田绿地比房子还多,有时微风轻轻吹来,脸上的凉意还掺杂一点青草味、炊烟味,缓慢,和乐,仿佛就这样一直待着,时间也不会留下走过的痕迹。现在想来,原来这些宁静的小村都是我爸与人较劲的战场,浓浓的火药,暗自爆发在纯然悠闲的乡间图像中。
连续剧
我家的连续剧每晚开演,比现在当红的虚拟实境连续剧早了好几年,我爸是导演,全家配有角色,身份不变,桥段重复。
尽管每日上映,身为演员的我,却依然难以入戏。吃完晚餐,马上抓紧零碎时间看电视玩玩具,虽然早过了卡通时间,还是盯着不是很懂的琼瑶爱情片猛看。故作悠闲,其实心里慌得很,暗自观察导演动作。他先是剔剔牙抠抠香港脚,然后翻翻电话簿算算今日的零余,那皱成一堆的百元钞票拖延时间,他一一摊开计算,一张、两张……。男女主角说着今生爱你永不渝,正猜想“永不渝”的意思,他突然起身,扭扭脖子,往楼下走去,我故意专注屏幕装作什么都不知,然而那双眼却传来一阵寒意,只能认命关上电视,下楼。
卡麦拉!
怕落入“歹戏托棚”,一心期待愈快结束愈好,但这速度连导演也不能掌控,决定于车上货物多寡。观望大台货车,是我首要步骤,如果货物剩得多就暗自欢呼,若剩得少就自认倒霉,反正美丽的夜晚,都献给这场只有演员没有观众的家族连续剧了。
第一场戏,导演不参与,由我和我姊领衔主演。导演拿起竹板,将高高在上的卫生纸箱扫落地面,砰,砰,砰,砰,整条走道布满道具,抗压性低的,落下时四边撞出长长裂口。我们用原子笔头划开胶带,拆封纸箱,卫生纸散落一地,拿着长塑料袋,一串五包,且记得,第一包要反着放,这样两头才见得到商标。导演第一次教戏时再三叮咛,看到一头空白的卫生纸串马上怒斥拆掉重包,然后检查我们打的结是不是活结,若是死结便换来一场叨念,这样别人怎么打开!必须留心所有细节,不可破坏戏的流畅完美。一箱两箱三箱倒出来,堆起来像一座小山,软软的模样叫人想钻在里头如弹簧床,但是他们的第二站不是房间,而是导演驾驶的大台货车上。
往往是我上车去,货车前面有一区专门放卫生纸,空间不大,屈身,弯腰,才能继续演出。我姊是支持者,将纸箱内刚刚包好的卫生纸递给我,依着舞台规划,左边是五十元区,右后方是九十元区,右前方则是高级破百区,开始走位,动作。我们俩可是合作无间,五十元再来两个,九十元再来三个,衔接流畅,毫无冷场,有时突然词穷了,原来是弹援用尽,目测还需要多少箱。在一旁忙碌的导演,听到演员陷入困境,又会回到主场来,提供材料,让戏继续进行。
第二场戏极为简单。空舞台转到货车的后面,打开铁门,放下铁板,斜状的木心隔板将全区分为左右两边。导演总先自导自演,才开始说戏,但久了演员也可看出端倪,马上就能抢戏。木心隔板下的木盒,左边是漂白水,右边是洗碗精,快步到后台木柜上取来,然后拿起导演自制的长铁棒,前头特制的弯钩和铁弧板,是必备的道具。木盒又深又狭,无人能钻,得先用弯钩取把手拉出,清理混乱的场景,然后,将一旁久候的新鲜货置于箱口,铁弧板与塑料罐弧度相合,紧密,推,归位。
再往左右两边看,木心隔板旁放置洗衣粉,但大小不同,四点五公斤与十公斤,要分得清楚。再往前,则是盐酸区,有烟的在右边,无烟的在左边,一目了然。来回在后台与前台之间,一包一箱运着,导演接手,搬上指定位置。搬家之后,房子变大了,舞台的界线扩张,演员们来回跑个几趟,便气喘吁吁,为维持演出速度质量,导演买了一台推车,可将所有物品放到推车上,一次解决。推车出现的当天,演员们皆报以热烈的掌声,邻居小孩也来凑热闹,站上推车要导演推着跑,好比飞翔。
最难的一场,便是最后杂物的处理。到此演员皆有疲态,有时导演也会好心提早收尾,要我们下场休息,但若剧情无法停顿,导演则会要求我们齐力完成。这阶段演员变成傀儡,拿几包垃圾袋,拿几罐洗发精,这些细节,是演员怎么也无法搞清楚的专业,一举一动,都是临时的台词,谁也猜不着,只能配合。我常常疑惑着导演怎么能够清楚这些琐碎的字句,拼凑成戏剧收尾的一刻,完不完美就看这场。等他关上铁门,空车又满,整齐的物品展现华美姿态,我们每天演出的成果,就等着明天到街上让人欣赏,或说,破坏。
当然,偶尔有客串来宾,通常是我妈,若在楼上无聊,戏胞痒了起来,便下楼参与。还有邻居的小孩,不过八九岁,特爱客串,甚至积极争取正式角色。厌倦每天例行的演出,我成了沾染职业病的老演员,什么都提不起劲,小孩们却等着我们打开电动门,扭开聚光灯,冲过来喊着:“阿伯,我要帮忙。”这是每天晚上的游戏,他们乐在其中,展现了高昂的兴致,包装搬运都快意,我当然是暗自欣喜的,剧情可以偷偷跑快一些,有时步调故意缓了些,嘘,别说我偷懒,只是想要把机会让给新进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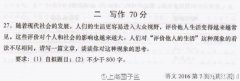

![[头条]:2016湖南高考作文题出炉 漫画作文 与分数有关](http://www.xigushan.com/uploads/allimg/160713/051FD3S_lit.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