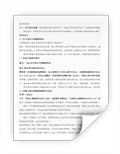周总理的干女儿孙维世是如何惨死的?
孙维世是如何惨死的?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女犯、夜半歌声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一九六八年八、九月份,我从北京看守所的“K字楼”搬到了五角楼。
在这个时候,在我们楼下的牢房里有个女犯不断的喊口号:“打倒野心家,保卫毛主席!”或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为这她没少挨打。听声音就知道:不一会儿还给她套上胶皮防毒面具,那东西不能戴得太久,一会儿就憋得喘不出气了。刚给她摘下来,她又喊:“真理是不可战胜的,野心家爬得再高,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她又被折腾、毒打,每天都是这样。有时候,半夜里看守都折腾累了,跟她同屋住的犯人也没劲再打她了。这时,她就小声的唱歌。有时会唱很久,直到哪个打手缓过劲来,再接着收拾她。她唱许多俄罗斯名歌,也唱《我们是民主青年》、《酸枣刺》、《行军小唱》等中国歌曲。至今我还记得她那远去的歌声:
“叮叮格儿,咙格儿咙;叮叮格儿,咙格儿咙。
战士们的心哪,战士们的心在跳……”
当时和我关一个牢房的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刘焕栋(信使)、李兰平(机要员),小李是四川的高干子弟,在揪斗陈毅元帅的时候,小李在后台负责看守他。
陈老总还和他聊了聊天,好像和他爸爸还认识……。
有天晚上,那女犯又唱起歌来,我悄悄地问小李:你猜她是什么人?小李说:肯定是干部子弟,或者是个干部家属。一般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唱这样的歌。我说:这咱们早就这样讨论过,我是让你猜她是谁?
他想了想,说:现在抓了那么多人,咱们怎么猜啊?我说:会不会是孙维世?
人们都听说她让江青给抓起来了。小李想了想说:“不会吧,如果是她,应该关到更高级的地方。”他是指她至少得关到秦城。当时我想他说的也有道理。
十年以后,我刚从监狱放出来,就去上海看受我连累也关进监狱十年的郑安磐,他父亲剧作家郑沙梅先生,三十年代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活动的时候,认识张春桥和江青。我们被抓的时候,郑老先生已经被专案组抓起来了。所以抓郑安磐的目的也是要让他坦白交待:是谁讲给他关于当年江青在上海的这些传闻、这些“反动谣言”?
在安磐家见到了孙维世的侄女孙冰,我们自然的谈到孙维世之死,我就告诉她,我在五角楼的那段故事。她和小李子的想法一样:“不会吧?我想姑姑准是关在秦城监狱。”我想也可能是这样,连叶浅予、黄苗子、郁风这些三十年代知名的艺术家都关在秦城,何况是孙维世呢。当时孙冰就说,她准备写一本书,记念爸爸孙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和姑姑孙维世,为他们伸冤,这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
她也劝我写本书留下一个历史记录。
那时,中国的政治气候还没有稳定下来,所以我说,我要等一等,再看看,等我想好了,会再来找她谈,好好交流一下。孙冰说:下次你来上海,也可能找不着我了。我很奇怪:
“为什么?你要搬到外地去呀!”
“我在上海也是住在一个远亲家,我都怕在北京不安全,那些过去的打手和刽子手,他们现在慌了。你哪儿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咱们要追究这些历史罪行,万一他们狗急跳墙,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杀人灭口。我现在就在设法出国去探亲,你也得好好想一想。”她说。
她这一席话,使我后脑勺阵阵凉风。我想起来,北京公安局到现在还不肯消毁我那一大堆档案材料。和我们算是同一个大案子的司徒慧敏之子司徒兆敦(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青年教师)的档案就给销毁了。可是,他们说我“里通法国”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所以我的档案不能烧,这就是说还“留下一个尾巴”。
我自此决定还是远走高飞,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变成“失去自由恐惧症”的患者了,而如今自然变成了个职业世界流浪汉。
二十年后,我在天涯另一隅的普林斯顿大学,遇见唐达献(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唐达成之胞弟),一起聊当年的囹圄之灾,他说:“当年我也关在半步桥,你们比我们先进去的,是当时一号大案,我们是另一种大案进来的,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
我们自然的谈到当时在看守所里关了哪些人,都见了谁。我告诉他,我在五角楼的时候,有一次放茅,由于犯人太多,看守忙不过来,把另外一个号子的犯人也放进卫生间来,见到我在外语学院附中的同学夏书林,他指着旁边一个愁眉苦脸的中年人,说这是冯基平(北京公安局局长)的“副官”,当初给咱们这些未决犯计划每天粮食的定量,就是他干的,冯基平划勾的,这回跟咱们一块挨饿,古话应验了,这就叫“作法自毙”。当时我问这干部:是不是定量太少了。他苦笑着说:那时哪会想到呢?觉得未决犯反正不干活,八两粮食差不多了。没想到这么难熬。
我又问他:那个在走廊里老喊“革命的同志们啊!”的那个人,准是和你一样,也是北京公安局的老干部吧?他默默的点点头。
我看他好像什么都知道,就又问他:“那个唱歌的女的是不是孙维世?”
他说:“也可能是。她三月份才进来,我们早就被打倒了。根本没权力去过问。我自己也觉着像。”叹了口气,接着说:“她这么闹,在这地方就活不长了。”
我和夏书林也都这么想。在监狱里,这么折腾的人,被看守说成是“属家雀的”─这种鸟气性大,进笼子就扑腾,就撞杆,不是找死吗?没听说谁养得活家雀。
此后,我们在监狱里的十年见过许多这样的真疯假疯的人,最后都死得很惨。
本来那唱歌的女士住在我们楼下,她轻声的夜半歌声,都字字入我耳。
◆《保尔·柯察金》女导演
我小时候,老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以下简称“青艺”)去玩,可是对孙维世的印象却很模糊,因为她和青艺延安来的那拨人,关系不是很密切。